【遏制细菌耐药白皮书】蔡常洁教授: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感染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
近年来,实体器官移植(solid organ transplant,SOT)是肝脏、肾脏、心脏、肺脏、胰腺等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虽然移植外科手术成功率已大大提升,但为了提高移植物存活率和更好的免疫耐受,SOT受者在术后需使用免疫抑制剂,且随着公民逝世器官捐献的增加,感染的发生率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自2015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移植器官的重要来源,供体来源的病原体感染成为SOT受者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大约有80%的SOT受者在移植术后出现过一次临床感染,接近40%的受者围手术期死亡原因是感染或其他并发症合并感染。
一、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药物合理应用
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病原体多来自于院内环境、受体或与供体相关。供体相关感染(doner-derived infection,DDI)发生率低,但死亡率可达50%以上。我国DDI发生率为1.02%,其中细菌感染占85.4%。目前认为受者高龄(>60岁)、营养不良、术前长期住院、多重耐药菌的定植或感染、留置导管、近期抗菌药物的使用(术前90天)会导致移植术后早期感染的发生。另外,术中移植器官的保存液污染、手术时间过长、出血量大、留置异物、吻合口漏、肠漏、移植器官灌注不良等是手术相关感染的危险因素。此外,术后大剂量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留观重症监护室时间或气管插管时间过长(>72小时)等术后相关因素同样会导致SOT术后感染。因此,术前供受体的感染筛查、术前供受体感染的有效控制、以及抗菌药物在围手术期的预防应用是减少SOT术后感染的重要措施。
(一)实体器官移植术后常见病原菌分布与耐药现状
SOT术后感染发生的部位、病原菌分布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目前Barchies等研究发现,SOT术后早期感染发生率占26.7%,总体以病原菌以G-菌为主,约占68%,常见的分离菌株为肺炎克雷伯杆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等。而G+菌中以屎肠球菌(57%)最为常见,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9%)。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细菌的耐药性也逐渐增强,出现了许多新的多重耐药(multidrug-resistant,MDR)、泛耐药(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XDR)甚至全耐药(pandrug-resistant,PDR)的“超级细菌”。作为免疫缺陷的人群,SOT受者一旦发生MDR细菌感染,病死率高达40%,多数患者死于呼吸或循环衰竭。常见耐药的阴性杆菌主要包括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XDRAB)、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XDRPA)、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β-lactamases,ESBLs)的肠杆菌、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杆菌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等;常见耐药的阳性球菌主要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VRE)。常见的感染部位包括肺部感染、伤口周围感染、泌尿系统感染(肾盂肾炎、膀胱炎)、血流感染、腹腔感染等。针对SOT受者,需要高度关注肺炎克雷伯杆菌,其分离率近年来呈逐渐上升的趋势。根据我国耐药细菌监测网的数据,肺炎克雷伯杆菌已在2017年呼吸道分泌物培养中超过了鲍曼不动杆菌,占据了首位,而且,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率也逐渐上升。耐碳青霉烯的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尤其是CRKP的发生率从2005年的3%上升至2018年28.6%,严重威胁SOT受者的存活率。此外,不同地域不同地区来源的人群菌株的耐药机制并不一致,如产生碳青霉烯酶(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s,KPC)或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NDM)-1是肠杆菌产生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最主要的两种机制,我国北方临床医院分离CRE以NDM-1菌株较多,而南方则以KPC型菌株更为多见。
(二)常见的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感染分析
1.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分析
(1)腹部感染:肝移植术后腹部感染的发生率高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发生率约为18%~37%,腹部感染大多数发生于移植术后1月内,主要包括切口感染、胆管炎、腹膜炎和腹腔脓肿等。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是导致感染的主要致病菌。随着抗生素的滥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感染也逐渐增多。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为主要处理方案,可选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等,疗效不佳时应该根据药敏结果或经验性地调整为碳青霉烯类;重症感染宜首选碳青霉烯类,经治疗临床稳定后可降阶梯为β-内酰胺类抗菌药/β-内酰胺酶抑制剂合剂,必要时需联合外科清创和引流治疗严重感染。
(2)肺部感染:肝移植术后肺部细菌感染的发生率仅次于腹部(可高达8%~23%)。由于肝移植术后第1周出现非感染的肺部并发症较多(肺不张、胸腔积液发生率可达86.7%,肺水肿发生率44.7%),持续的肺部非感染性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医院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其致病菌中以肠源性G-杆菌最常见,如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等,此外耐药菌株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杆菌、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也逐渐增多。术后可早期进行呼吸锻炼,减少肺不张引起的肺部感染,同时加强气道管理、严格控制呼吸机使用时间可以进一步降低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3)血流感染:细菌引起的血流感染主要发生在肝移植术后的1月内,目前研究表明肝移植术后血流感染的病死率达16%,合并脓毒性休克的肝移植患者死亡率高达50%。Hand J等报道G-杆菌造成的血流感染更为常见,以大肠埃希菌与肺炎克雷伯杆菌为主;在G+致病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与肠球菌占较大比例。早期拔除留置导管可减少血流感染的风险。
(4)泌尿系感染:在肝移植术后细菌性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约为2%,主要危险因素为受体年龄、性别、糖尿病病史、既往泌尿系感染病史、导尿等。最常见的病原体为G-杆菌,如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尽早拔除尿管可以减少泌尿系感染的机会。
2.肾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分析
(1)泌尿系感染:占肾移植患者细菌感染的大部分(约45%~75%),可能引起严重的后遗症,包括脓毒症、急性排斥、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甚至增加死亡风险。泌尿系感染主要来源于G-杆菌(高达90%),包括大肠埃希菌、梭状芽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在G+菌中,肠球菌最为常见,其他细菌(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尿毒症棒状杆菌)较少被报道。治疗应根据病原学分析、患者的特征、风险因素、地域特征以及当地移植中心流行病学进行经验性治疗。首先对复发或复杂性尿道感染的肾移植患者,需及时处理原发病(如瘘管、结石等)。对于无并发症的泌尿系感染,经验性治疗方案包括氟喹诺酮类药物(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类药物,在怀疑有肠球菌病因的情况下增加阿莫西林或硝基呋喃妥因。治疗时间应限制在5至7天,以减少耐药菌株的风险。对于复杂的泌尿系感染,应静脉使用抗生素,并根据病原学、药敏结果迅速调整治疗方案(即静脉注射头孢类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或美罗培南等)。如果是肾盂肾炎,必须延长治疗时间,至少要延长到14~21天。
(2)肺部感染:肾移植的患者肺部感染时获取病原学证据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严重/复发的患者),一般可以通过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液获得,必要时可进行肺活检明确病原学诊断。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的细菌包括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支原体属、军团菌属和衣原体属,此外假单胞菌属、肠道G-杆菌和链球菌属多在移植早期发生。经验性治疗应考虑患者临床和病原学特征进行调整。对于术后门诊患者,通常建议使用β-内酰胺类药物或喹诺酮类药物作为初始治疗;根据患者的病史和临床情况,可考虑加入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或假单胞菌属的药物。对于住院患者,强烈推荐使用β-内酰胺类药物(覆盖MRSA和假单胞菌属)和另外一种对细胞内病原体有直接作用的药物(覆盖支原体和军团菌属)。
(3)结核杆菌与诺卡氏菌感染:肾移植患者是结核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具有很高发病率和不良的预后,包括移植器官失功。根据现有的指南,最好是延长异烟肼的疗程,并严格随访以监测不良反应。异烟肼是治疗的基石,但要注意其与其他药物(如利福平)联用会带来肝毒性风险。所有分枝杆菌感染都对移植物生存率和患者死亡率有很大影响,因此需要早期、联合、规律、全程治疗。诺卡氏菌是一种机会性感染菌,临床感染只发生在免疫力低下的宿主身上。肾移植人群中的发病率一般在3%以上,根据地理区域、移植类型(肺部受体的风险增加)和免疫抑制药物的应用有很大差异,一般认为近期有巨细胞病毒感染史、激素治疗史、高剂量他克莫司用药史的患者风险增加。肺部是感染的主要部位,其次是皮肤/软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大剂量磺胺类药物是治疗的基础,一般治疗方案为大剂量复方磺胺甲恶唑(15mg/(kg·d))或利奈唑胺,持续3~6个月。必要时可联合大剂量的氨苄青霉素。
3.肺移植术后细菌感染分析
在所有SOT受者中,肺移植患者1年内感染发生风险最高,75%的患者在肺移植术后的前3个月会患上细菌性肺炎,1个月内因感染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19.2%。其中细菌感染占最大部分,约69%。G-菌感染率较G+高,常见为肺炎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G+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多见。在肺移植感染的所有细菌种类中铜绿假单胞菌和对甲氧西林敏感的葡萄球菌(methicillin-sensitive Staphylococcus aureus,MSSA)最常见,占56%。
肺移植术后细菌感染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胸闷、气促等,对于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建议立即行支气管镜检查同时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必要时可经支气管镜活检,明确病原学证据。
肺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预防主要从控制感染来源、降低感染风险、保护易感人群等方面执行。预防细菌性感染的药物可选择覆盖G-菌(如假单胞菌)和G+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治疗时间1~2周,直至痰培养或肺泡灌洗液呈阴性。但目前仍然没有关于肺移植术后抗菌治疗的全面指南,根据目前专家共识,在肺移植围手术期使用抗菌药物是必需的。我国肺移植术后常见的致病菌为MDR肺炎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其次为真菌和病毒。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病原学和药敏结果调整抗感染方案,必要时可加用抗生素气道雾化,提高抗菌药物在肺泡浓度。
4.心脏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分析
心脏移植术后60%以上的感染为细菌感染,主要感染为医院获得性肺炎、社区获得性肺炎和泌尿系感染。移植后的前三个月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最高。
在心脏移植术后感染的病原学中,耐药菌所致的感染比例越来越高,有文献报道,G-杆菌中最常见的耐药菌是泛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CRAB)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除此之外还有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杆菌的报道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此外,纵隔炎和胸骨手术伤口感染的发生率接近2.5%,大多数是由葡萄球菌属引起的。在西班牙的一项多中心研究中,MRSA是心脏移植后手术切口部位感染的常见病原菌之一。
心脏移植术后G-菌感染中,针对耐碳青霉烯的肺炎克雷伯杆菌,可以选择替加环素、多黏菌素、β内酰胺酶抑制剂等。鲍曼不动杆菌对替加环素与多黏菌素耐药率较低。而针对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单胞菌,首选复方磺胺甲恶唑,同时可以联合米诺环素等治疗。G+球菌感染中,对于合并MRSA感染的患者,可以根据药敏结果选择耐药率较低的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
5.胰腺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分析
胰腺移植是唯一有机会治愈1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方法。胰腺移植患者的细菌感染发病率在术后第1个月比较高,有超过1/4(25.5%)的胰腺移植患者出现细菌感染。手术部位感染是最常见的感染类型,占感染患者的42%,其次是泌尿系感染(38%),以及导管相关的血流感染和其他感染。从流行病学上发生率最高的G+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35%)与屎肠球菌(47%)。G-菌为产ESBLs的肠杆菌(10%)。根据目前病原菌流行病学结果,在治疗过程中应该选择覆盖肠球菌和肠杆菌的抗菌药物,同时定期留取病原学标本送培养,根据药敏结果调整抗感染方案。
(三)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治疗策略
SOT术后感染的诊断主要依赖于临床表现和病原学检查,但由于移植术后患者应用免疫抑制药物,临床表现通常不典型,少见伴随发热、白细胞升高等症状,病原学检查阳性率低。经验性抗菌药物应该根据当地或移植中心的细菌流行病学数据、患者的抗菌药物使用史及细菌定植情况来选择。目标治疗应基于药敏结果、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药物不良反应及相互作用、适应证等综合评估。对于抗生素的疗程,需根据病原学证据、感染部位、治疗效果、药物不良反应进行个体化选择。此外,感染源的控制同样非常重要,需尽量移除感染的植入物,通畅引流。
1.SOT受者的抗生素治疗原则
(1)应根据药敏结果选用敏感的抗生素,若所有药物均不敏感,应根据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选择接近敏感折点的药物。
(2)对于SOT受者MDR感染,不仅需要增加抗生素的治疗剂量,更需要联合用药。
(3)应该根据药动学和药代学原理设定给药方案,包括增加抗生素剂量、增加抗生素次数、延长抗生素滴注时间。
(4)应根据患者年龄、肝肾功能、体表面积等对抗生素剂量进行适当调整。
(5)应在抗感染治疗的同时积极处理原发病、控制感染源,尽可能消除感染灶。
2.SOT受者MDR感染的常用药物
(1)β-内酰胺类抑制剂与合成制剂:多为合成制剂,代表药物为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等。β-内酰胺类抑制剂能够抑制β-内酰胺酶的水解作用,临床上常用于覆盖常见的G-杆菌、耐药的G-杆菌。当治疗MDR鲍曼不动杆菌时,舒巴坦的剂量上限可增加至6~9g/d,同时可以延长每次给药时间,联合碳青霉烯类、多黏菌素等药物。对于耐碳青霉烯的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他啶单药耐药或其他MDR的G-杆菌导致的感染,可以使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
(2)碳青霉烯类:常见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包括美罗培南、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厄他培南等。碳青霉烯类药物对G-菌和多数厌氧菌有强大的抗菌作用,包括产ESBLs和AmpC-β内酰胺酶的致病菌。此外,对于部分MIC值不高的耐碳青霉烯肠杆菌,可以通过增加用药剂量、延长用药时间和联合用药达到治疗效果。
(3)替加环素:替加环素是甘氨酰环类抗生素,可以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对耐碳青霉烯的细菌具有抗菌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CRE、XDR鲍曼不动杆菌和其他肠球菌所致的腹腔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和呼吸道感染等。替加环素组织分布广,但血液中药物浓度较低,不适合单药治疗血流感染,一般推荐双药或三药联合治疗,常与多黏菌素类、β-内酰胺类抑制剂与合成制剂或氨基糖苷类联合治疗。
(4)多黏菌素:多黏菌素一般分为两类:多黏菌素B和黏菌素(多黏菌素E)。多黏菌素主要用于各种XDR的G-杆菌治疗,尤其是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多黏菌素单药治疗效果一般,常存在异质性耐药,常需要联合例如碳青霉烯类、替加环素等抗生素治疗,可表现协同作用。若合并肺部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杆菌或其他G-的MDR感染,可尝试予以黏菌素雾化吸入治疗。由于该类药物肾毒性、神经毒性等不良反应发生率高,对于肾移植或其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严密监测肾功能,必要时可监测药物浓度调整剂量。
(5)氨基糖苷类: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是抑制蛋白质合成的静止期杀菌性抗生素。其以抗需氧G-杆菌、假单胞菌属、结核菌属和葡萄菌属为特点,由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在发挥抗菌作用时必须有氧参加,所以对厌氧菌无效。常用药物有阿米卡星、妥布霉素等。氨基糖苷类药物对CRE的血流感染具有较好作用,当一线药物治疗无效时氨基糖苷类可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泛耐药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或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但氨基糖苷类药物具有较强的肾毒性、耳毒性,用药期间除严密监测肾功能外还需了解患者的听力变化。
(6)磷霉素:磷霉素为CRE的二线用药,可与多黏菌素、替加环素、β-内酰胺类抑制剂与合成制剂、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等联合治疗泛耐药菌引起的重症感染。因为磷霉素需经肾脏排泄,肾移植及肾功能不全患者需根据病情减量用药。
(7)四环素类:临床上常使用米诺环素,其对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
二、实体器官移植术后侵袭性真菌病的用药
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IFD)是指真菌侵入人体,在组织、器官或血液中生长、繁殖,并导致炎症反应及组织损伤的疾病。尽管侵袭性真菌感染在SOT中的发生率低于细菌和病毒感染,但它仍是移植术后死亡的重要原因。
SOT受者IFD的发生率和发生时机因移植器官类型和抗真菌预防药物的使用等因素而异。据国外流行病学调查,念珠菌(假丝酵母菌)是SOT受者术后IFD中最常见的病原菌(占53.0%~59.0%),好发于移植术后前几个月内,尤以腹腔SOT受者更常见。曲霉菌次之(占19.0%~24.8%),但在肺移植受者中以曲霉菌感染最为常见,且其好发时间与感染部位有关,气管支气管或吻合口曲霉菌感染通常发生在3个月内,其他形式的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则稍迟,多发生于术后6~12个月。少部分为隐球菌、接合菌和其他丝状真菌,隐球菌感染多见于肾移植,一般发生于移植后16-21个月,属于典型的晚发感染(表1)。
不同于其他患者群体,SOT受者术后需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且不同的移植器官受者群有其特殊危险因素,以及移植的医疗技术环境等,构成了SOT受者IFD的高危因素。抗真菌药物主要有三大类:三唑类(氟康唑、伏立康唑、泊沙康唑)、棘白菌素类(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多烯(两性霉素B脱氧胆酸和两性霉素B脂质制剂)。对疑似或确诊的IFD进行经验性治疗时,必须考虑到先前接触特定类别的抗真菌药物及过去90天内的经验性治疗,这些可能预示着对某类药物的耐药性。针对不同病原菌及不同移植器官特点,IFD的预防与治疗用药不尽相同。
表1:不同移植器官的真菌感染类型发生率

(一)实体器官移植受者IFD预防用药
侵袭性念珠菌病是SOT中最常见的感染,但侵袭性曲霉菌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考虑到它们具有相同的风险因素,必须在某些移植人群中结合起来制定预防策略。对于肾、心、肺移植,普遍认为不必常规预防念珠菌感染,小肠移植和胰腺移植受者则需使用氟康唑预防念珠菌病,预防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危险因素的持续时间,建议胰腺移植受者至少1~2周,肠道移植受者至少4周。存在高危因素的肝移植受者应接受抗真菌预防,选择哪种药物仍有争议,推荐用药包括棘白菌素类和两性霉素B脂质体。存在高危因素的心脏移植受者,可以采用棘白菌素类、伊曲康唑或泊沙康唑预防IFD。肺移植受者普遍接受对曲霉菌预防,在两性霉素B雾化吸入同时予以泊沙康唑、伊曲康唑或伏立康唑。
(二)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念珠菌病
念珠菌感染主要表现为念珠菌血症和侵袭性念珠菌病。在持续发热、念珠菌定植或存在念珠菌感染危险因素的情况下,当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经验性治疗疑似侵袭性念珠菌病可从使用棘白菌素开始,血流动力学稳定长达2周的情况下可使用氟康唑。
(1)念珠菌血症:对于念珠菌血症,建议应用棘白菌素类药物作为初始治疗(卡泊芬净:负荷剂量70mg,维持50mg/d;米卡芬净:100mg/d)。对于氟康唑敏感的非危重念珠菌感染,可用氟康唑替代治疗[首剂800mg(12mg/kg),维持400mg/d(6mg/kg)],当需同时对霉菌感染进行预防治疗时,也可以考虑使用伏立康唑。当念珠菌可疑对三唑类和棘白菌素耐药,可使用两性霉素B脂质制剂3~5mg/(kg·d),但必须注意其肾毒性。对于中性粒细胞减少或粒细胞缺乏的SOT受者,一旦出现念珠菌血症,必须使用棘白菌素类或两性霉素B脂质体进行治疗。
所有念珠菌血症患者应在治疗的第一周内进行眼底镜检查。建议每日进行血培养并尽早拔除深静脉导管,念珠菌血症的治疗应维持到血培养阴性后至少2周或更长,直到侵袭性念珠菌病的所有症状和体征消失。
(2)尿路念珠菌感染:无症状的SOT受者念珠菌尿症无需治疗,但对于有症状的念珠菌尿路感染、中性粒细胞减少或即将接受泌尿外科手术等存在感染播散高危因素患者,则需要接受抗真菌药物治疗。对氟康唑敏感的菌株,应用氟康唑[200 mg/d或3 mg/(kg·d)]治疗2周;如对氟康唑耐药(光滑念珠菌),可予两性霉素B脱氧胆酸或氟胞嘧啶治疗7~10天。棘白菌素类在尿液浓度较低,因此不推荐在尿路念珠菌感染中使用。
(3)气管支气管念珠菌感染:肺移植患者术后出现气道或吻合口念珠菌感染,可使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雾化吸入(5mg,每日2~3次),联合应用棘白菌素类药物治疗。
(4)念珠菌心内膜炎:对于念珠菌心内膜炎,无论是原发性感染还是人工瓣膜感染,都建议在一周内进行手术。治疗用药选择两性霉素B脂质体[5 mg/(kg·d)]或氟胞嘧啶[25 mg/(kg·6h)],持续6~8周,病情稳定后序贯以氟康唑治疗。
(5)口咽及食道念珠菌病:轻症口咽念珠菌病可用局部抗真菌药物(克霉唑或制霉菌素)治疗,中至重度患者需全身使用三唑类(氟康唑);氟康唑顽固性感染可能需要使用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或伏立康唑。重症患者静脉使用两性霉素B脂质制剂或棘白菌素。食道念珠菌病可口服氟康唑治疗。对于氟康唑难治性感染,可使用伏立康唑、泊沙康唑或两性霉素B脂质制剂。
(6)眼部念珠菌感染:未获得药敏结果之前,可应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单药或联合氟胞嘧啶治疗,不推荐使用棘白菌素类。若感染累及玻璃体,除全身治疗外,建议行玻璃体切除术或玻璃体内注射两性霉素B。
(三)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曲霉病
曲霉菌是肺移植受者中最常见的侵袭性真菌感染。对于强烈怀疑侵袭性曲霉病的SOT受者,及早开始抗真菌治疗至关重要,应根据曲霉类型、移植类型、受体情况、使用的免疫抑制剂进行个体化抗真菌治疗,减少免疫抑制是重要的辅助治疗。首选伏立康唑[负荷剂量6 mg/kg,维持剂量4 mg/(kg·12h)]初始治疗侵袭性曲霉病,两性霉素B脂质体[起始小剂量0.5mg/(kg·d),逐渐递增至3~5 mg/(kg·d)]可作为替代,泊沙康唑主要用于对其他一线抗真菌药物无效或耐药的治疗,棘白菌素类通常单独或联合用于挽救性治疗。由于SOT受者往往使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与三唑类药物具有相互作用,因此必须根据血药浓度调整二者剂量,建议对所有接受三唑类药物治疗的SOT患者进行治疗性药物监测(TDM),初始使用三唑类时,将CNI类药物的剂量减少1/3至1/2。
对于病情严重患者,推荐静脉使用伏立康唑并监测其血药浓度,使其维持在2~4mg/L,用药时注意监测肝毒性,对于肝移植受者尤需注意其与免疫抑制剂的相互作用,初始治疗失败可加用卡泊芬净联合治疗。存在伏立康唑禁忌时,推荐使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但需注意其肾毒性。对于重症肺炎或播散性疾病的危重患者,在确保伏立康唑治疗浓度的基础上,联合卡泊芬净[负荷剂量70mg/d,维持剂量50mg/d]作为初始治疗。肺移植患者的曲霉菌定植必须接受治疗,推荐使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25mg/d雾化治疗7天,继之25mg/72h雾化治疗]并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清除坏死碎片。对于结节性或溃疡性气管支气管炎,推荐使用伏立康唑加脂质雾化制剂。
SOT受者侵袭性曲霉病的用药需根据临床表现和高分辨率增强CT监测治疗效果,治疗时间取决于对治疗的反应、患者的基础疾病及免疫状态,通常至少需持续6-12周。
(四)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隐球菌病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播散性感染或中重度肺部感染患者使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0.7~1.0 mg/(kg·d)]或者联用氟胞嘧啶[100 mg/(kg·d)]作为诱导治疗,连用2周;继之使用氟康唑(400~800 mg/d)作为巩固治疗,连用8周;最后用氟康唑(200~400mg/d)维持治疗6~12个月。局灶性肺部感染或无症状患者采用氟康唑400 mg/d[6 mg/(kg·d)]治疗,疗程6~12个月。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需减少氟胞嘧啶和氟康唑的剂量,为减少氟胞嘧啶的不良反应(骨髓抑制和肾毒性),建议监测氟胞嘧啶血药浓度水平(给药后2小时30~80µg/mL)。如若可能,应在治疗过程中降低免疫抑制,但需注意这可能导致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immune reconstitution inflammatory syndrome,IRIS)的出现。
(五)实体器官移植受者耶氏肺孢子菌肺炎
对于SOT受者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治疗的首选用药为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TMP-SMX)。严重感染时,静脉使用喷他脒可作为TMP-SMX后的二线药物,但需注意其毒性反应,包括胰腺炎、低血糖和高血糖、骨髓抑制、肾功能衰竭和电解质紊乱,胰腺移植受者中应避免使用喷他脒。出现低氧血症时,最好在开始抗真菌治疗的72小时内辅以激素治疗。治疗持续时间至少为14天,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当治疗反应不良时,需考虑到可能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如合并巨细胞病毒(CMV)肺炎可能需要抗病毒治疗。
(六)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毛霉菌病
毛霉菌病的治疗包括坏死组织清创,纠正中性粒细胞减少,降低免疫抑制与应用抗真菌药物。首选两性霉素B脂质体[起始剂量5mg/(kg·d),如果耐受可增至12.5 mg/(kg·d)。泊沙康唑作为存在两性霉素B禁忌的二线治疗。
三、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病毒感染的用药
由于手术、术后并发症和免疫抑制剂的长期大量应用,SOT受者各种病原体感染的机会显著增加。中期(移植后31~180天)是来自供体器官、血液制品和受者体内潜在的危险因素再次活化感染开始的最典型时间,在此期间,诸如巨细胞病毒及EB病毒等病毒感染达到高峰。在晚期(移植后180天以上),感染风险因免疫抑制和暴露情况而不同,但相较于中期,病毒感染风险有所下降。本节主要讨论移植术后抗病毒用药的时机和策略。
1.巨细胞病毒(CMV)SOT受者病毒感染中,以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最常见,SOT受者感染CMV的临床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CMV感染、CMV病、CMV肺炎。当前常用于预防和治疗CMV的药物主要有:缬更昔洛韦、更昔洛韦、伐昔洛韦、膦甲酸钠、西多福韦等。缬更昔洛韦、口服更昔洛韦、静脉滴注更昔洛韦均为一线用药。静脉滴注更昔洛韦为抗CMV病或CMV综合征的一线治疗用药,可以用于普遍性预防(universal prophylaxis)和抢先治疗(pre-emptive therapy)。而伐昔洛韦仅用于肾移植受者。
移植术后存在CMV感染风险的SOT受者应接受普遍性预防。普遍性预防最常用的是更昔洛韦静脉滴注和缬更昔洛韦口服,缬更昔洛韦的高生物利用度和较低的药片负担使其成为成年SOT受者普遍性预防优先选用药物。缬更昔洛韦预防的推荐剂量是每日一次900mg(用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由于存在白细胞减少的风险,一些移植中心使用“小剂量”缬更昔洛韦预防药物(即450mg口服),但这已被证明与耐药CMV的出现有关,特别是对中高危受者(即供者阳性/受者阴性,D+/R-)。替代方案包括静脉滴注更昔洛韦或伐昔洛韦(但仅用于肾移植受者)等。普遍性预防方案在移植后10日内即开始,用药周期一般为3~6个月。在移植后普遍预防期间,需每周监测CMV DNA,4周后如果连续两次为阴性,可以改为每2周监测1次,共监测12周。若监测结果持续为阳性,可给予治疗剂量或联合二线用药(建议根据基因突变检测结果选择用药),持续用药直至结果转阴。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和CMV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也可用于心、肺移植、小肠移植受者的辅助性预防。另外对CMV D+/R-而言,不建议使用CMV特异性预防。采用抢先治疗方案需要定期监测CMV血清指标,在明确CMV病毒复制时立即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直至CMV血清指标转阴,并持续CMV血清指标监测至少至移植后第12周。
由于SOT术后CMV感染的防治广泛采用更昔洛韦,致使对更昔洛韦耐药的CMV越来越普遍,但目前针对更昔洛韦耐药的治疗方案十分有限。SOT后耐更昔洛韦CMV感染的发生率为0%~3%。耐药的危险因素包括长期小剂量抗病毒药物治疗、D+/R-状态、强烈的免疫抑制和肺移植。在长时间服用抗病毒药物后出现难治性CMV感染或疾病的患者,以及在至少2周适当剂量抗病毒治疗后仍无反应的患者,应怀疑具有耐药病毒。此时需行基因检测以明确是否具有耐药性,在疑似对更昔洛韦耐药的患者中应进行UL97基因型检测,在疑似对更昔洛韦、膦甲酸和西多福韦耐药的患者中应进行UL54基因型检测。对于难治性或耐药性CMV感染和CMV病的患者,建议谨慎减少免疫抑剂的用量,可将钙神经蛋白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类药物换为西罗莫司,也可将霉酚酸类药物换为咪唑立宾。CMV耐药的经验性治疗包括加大静脉滴注更昔洛韦剂量(增至10 mg/kg,每日2次)或联用全效剂量膦甲酸钠。具体治疗参考CMV基因型检测结果,必要时可选择西多福韦。
CMV肺炎是SOT受者最常见的感染性并发症之一。CMV肺炎一旦发生,病情进展迅速,患者往往在短期内死于呼吸衰竭,病死率高达30%~50%。CMV肺炎的预防方案也分为普遍预防和抢先治疗,根据中国人对药物耐受性的特点,抢先治疗的推荐剂量为:体重>50 kg者,以900 mg(每日早上)和450 mg(每日晚上)口服;体重<50 kg者,450 mg口服(每日2次),连续口服2~3周后,或CMV-DNA转阴后,剂量减半。CMV肺炎的治疗方案分为诱导治疗及维持治疗,诱导治疗为更昔洛韦静脉滴注,起始治疗剂量为每次5mg/kg,每日2次,持续治疗2~4周,或持续至血液中CMV-PCR检测连续2次均为阴性后,才考虑改为口服;维持治疗初期为更昔洛韦静脉滴注,持续治疗2~3周。一旦临床表现及 CMV病毒载量得以充分控制后,可以将更昔洛韦剂量减半或改为缬更昔洛韦口服持续治疗,持续至血液中CMV-PCR检测连续2次均为阴性后,再持续治疗4周。治疗期间以及停药2个月内需每周检测CMV-PCR,停药2个月后,每2~4周检测CMV-PCR。对于伴有危及生命的CMV肺炎或伴有其他形式严重疾病的SOT受者,可以在现有抗病毒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丙种球蛋白或CMV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2.乙型肝炎病毒(HBV) SOT受者是HBV的易感人群。在肝移植受者中,74.79%的患者既往合并肝炎病毒感染,其中HBV占71.25%。对于肝脏以外的肾脏、心脏、胰腺等其他器官移植受者而言,供体来源的HBV感染常导致术后HBV的新发感染。无论是既往HBV感染还是供者来源的HBV感染,SOT术后HBV再激活的风险都较高。因此,SOT术后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HBV的再感染的预防和治疗。为了预防和治疗肝移植术后HBV的再感染,过去临床上多采用拉米夫定(lamivudine,LAM)联合小剂量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hepatitis B immune globulin,HBIG)为基础的治疗方案。虽然LAM的疗效稳定,但是其最大的缺点是可以诱导HBV基因变异,导致耐药率随用药时间延长逐年上升。近年,核苷酸类似物(NAs)如恩替卡韦(entecavir,ETV)、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替比夫定(telbivudine,LDT)、阿德福韦酯(adefovir,ADV)的出现,为防治肝移植术后HBV再感染提供了更多选择。
接受HBsAg阳性供肝的受者术后治疗方案采用NAs联合大剂量HBIG方案:NAs选用ETV或ADV联合LAM;术中无肝期应用大剂量HBIG 8000 U,术后1周内每日HBIG 2000 U,此后根据抗-HBs滴度调整剂量及输注方式,逐渐减量直至低剂量HBIG维持或停药。术后,应用NAs联合小剂量HBIG方案预防HBV再感染。宜选用高耐药基因屏障NAs药物,如ETV或TDF。术后HBIG的推荐使用方案为:术后前3天,静脉注射1000 U,每日1次;此后肌肉注射400 U,每日1次,逐渐减量,并根据抗-HBs滴度调整HBIG剂量和频率。术后随访密切监测HBsAg、HBV DNA及抗-HBs滴度,若抗-HBs滴度突然降低或难以维持常预示HBV再感染。
对于诊断明确的肝移植术后HBV再感染或新发感染,首先常规予以护肝及营养支持等治疗。除HBV再感染导致的暴发型肝炎考虑再次肝移植外,多数患者可停用HBIG,并选用高耐药基因屏障NAs药物继续治疗,如ETV或TDF等。肝移植受者HBV再感染或新发感染的抗HBV治疗需持续终生,尚无停药指征。
肾移植等其他器官移植术后HBV再感染的治疗与肝移植类似。当肾移植等其他器官移植术后发现HBV DNA阳性时,多采用NAs进行抗病毒治疗,直至HBV DNA转阴。如合并肝功能异常还需进一步行护肝等对症治疗。同时,应密切监测HBV耐药基因突变,一旦发现耐药需及时调整用药。肾移植等其他器官移植术后HBV感染的预防需根据患者HBV血清学情况制定。如果患者既往无HBV感染的血清学证据,且未接种疫苗,术前应接种HBV疫苗;已接种过疫苗者应定期监测抗-HBs滴度。若肾移植受者HBsAg或HBV DNA阳性,在决定肾移植后应立即开始服用高耐药基因屏障NAs药物(ETV或TDF),提倡在移植前进行肝活检,并在组织学正常后行移植手术。
3.EB病毒(EBV) SOT术后EBV感染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是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PTLD),在移植后1年内即免疫抑制最强烈的阶段其 EBV相关PTLD的发生率最高,与器官移植物类型及受者特异性危险因素有关。PTLD为一组异质性病变,包括多种组织病理学类型,从反应性多克隆B细胞良性增生到恶性侵袭性淋巴瘤,超过70% PTLD的发生与EBV感染相关。肾移植受者 PTLD发生率最低,多器官移植和肠移植发生率最高,PTLD发生与移植器官中淋巴组织的密度相关。不同器官组织中存留的淋巴组织数量不同,PTLD的发生率亦不尽相同。
EBV感染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非PTLD EBV感染综合征和EBV相关PTLD两类。当前尚无明确证据支持SOT高危受者(供者阳性/受者阴性,D+/R-)常规预防性应用抗病毒药物(如阿昔洛韦、更昔洛韦等)能够降低PTLD发生风险。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受者仍可出现EBV载量升高并发生PTLD。而输注免疫球蛋白可以在短期内降低PTLD的发生风险,但证据有限。有研究证实,常规监测病毒载量升高时采用抢先治疗策略可以降低PTLD的发生率。抢先治疗策略包括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加用抗病毒药物,加用或不加用免疫球蛋白,还包括给予低剂量利妥昔单抗(rituximab,RTX)和过继免疫治疗。减少免疫抑制剂剂量是PTLD治疗的第一步,应尽早开始。另外多数EBV相关PTLD来源于B细胞并表达CD20,提供了抗B细胞单克隆抗体(抗CD20单抗)RTX的治疗靶点,这与标准CHOP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疗效相似,但耐受更好,无严重感染相关的不良反应及治疗相关的死亡。但RTX单药治疗容易复发,远期疗效不理想。对RTX治疗反应差的病例以及病理类型为T细胞淋巴瘤、Burkitt PTLD或霍奇金淋巴瘤的病例均应积极考虑化疗,或RTX联合化疗,通常为CHOP或CHOP样方案。为了提高RTX单药治疗的长期有效性并避免单纯化疗的不良反应,对于减少免疫抑制剂剂量无效的CD20阳性的PTLD患者,可采用RTX加化疗如R-CHOP方案联合序贯治疗。有研究将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联合更昔洛韦或阿昔洛韦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治疗早期PTLD。
4.BK病毒(BKV) 近年来,随着SOT手术的广泛开展,新型强效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以及检测手段的革新,BKV感染率不断升高。肾移植术后BKV感染率升高尤为突出,由其导致的BKV性肾病(BKV nephropathy,BKVN)已成为移植肾失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他器官移植受者罕见BKV血症和BKVN。对于已确诊的BKVN受者,应将降低免疫抑制剂剂量作为首选干预措施:(1)降低免疫抑制剂血药谷浓度和剂量,血药谷浓度他克莫司<6 ng/mL、环孢素<150 ng/mL、西罗莫司<6 ng/mL,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剂量≤1000 mg/d;(2)将他克莫司调整为低剂量环孢素,或将CNI调整为低剂量西罗莫司,或将MMF调整为来氟米特或低剂量西罗莫司。在明确BKVN诊断后1个月内即进行干预治疗的受者,其1年移植物存活率高于未进行干预治疗或治疗时间延迟的受者。在已经充分降低免疫抑制剂剂量的情况下,血液BKV DNA载量仍持续升高,应考虑加用抗病毒药物,主要有:来氟米特、西多福韦、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等,但这些抗病毒药物尚需大型、前瞻、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以证实其疗效及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中国实体器官移植手术部位感染管理专家共识(2022版)[J].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2022,15(03):164-175.
[2] 李钢,药晨.器官移植术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诊疗规范(2019版)[J].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2020,8(02):81-85+78.
[3 ]巨春蓉,韦兵,练巧燕,陈奥,徐鑫,黄丹霞,陈荣昌.实体器官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肺炎的防治策略——ATS巨细胞病毒肺炎的诊治指南解读[J].器官移植,2019,10(01):88-90.
[4] 石炳毅, 巨春蓉: 器官移植受者侵袭性真菌病临床诊疗技术规范(2019版) [J],器官移植, 2019; 10(03):227-236.
[5]石炳毅,张永清,孙丽莹.器官移植受者EB病毒感染和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临床诊疗规范(2019版)[J].器官移植,2019,10(02):149-157.
[6] 石炳毅,范宇.器官移植受者BK病毒感染和BK病毒性肾病临床诊疗规范(2019版)[J].
器官移植,2019,10(03):237-242.
[7] 石炳毅,肖漓,孙丽莹.器官移植受者巨细胞病毒感染临床诊疗规范(2019版)[J].
器官移植,2019,10(02):142-148.
[8]李钢,石炳毅,巨春蓉,孙丽莹.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感染诊疗技术规范(2019版)——总论与细菌性肺炎[J]. 器官移植,2019,10(04):343-351.
[9] 李钢,石炳毅,巨春蓉.器官移植术后耐药菌感染诊疗技术规范(2019版)[J].器官移植,
2019,10(04):352-358
[10]《美国移植协会〈实体器官移植感染疾病诊疗指南〉 2013 年第 3 版介绍》,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第2卷第3期(2014年5月).
[11] 《美国移植协会〈实体器官移植感染疾病诊疗指南〉2013年第3版介绍(续二) 实体器官移植中供体来源的感染》,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第2卷第5期(2014年9月).
[12] Kinn PM, Ince D. Outpatient and peri-operative antibiotic stewardship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Transpl Infect Dis. 2022 Oct;24(5):e13922.
[13] So M, Hand J, Forrest G, et al. White paper on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Am J Transplant 2022; 22:96–112.
[14] Hand, J. The time is now: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Curr Opin Organ Transplant. 2021;26:405-411.
[15] Neofytos D, Garcia-Vidal C, Lamoth F, et al: Invasive aspergillosi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 patients: diagnosis, prophylaxis, treatment, and assessment of response. BMC Infect Dis 2021; 21(1):296.
[16]SEN A, CALLISEN H, LIBRICZ S, et al. Complications of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cardiovascular, neurologic, renal, and gastrointestinal[J]. Crit Care Clin, 2019, 35(1):169-186.
[17] van Delden C,Stampf S,Hirsch HH,et al. Burden and timelin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first year after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the Swiss Transplant Cohort Study[J]. Clin Infect Dis,2020,71 ( 7) : e159 - e169.
[18] Coiffard B, Prud'Homme E, Hraiech S, et al. Worldwide clinical practices in perioperative antibiotic therapy for lung transplantation. BMC Pulm Med. 2020;20(1):109.
[19] Tsikala-Vafea, M.; Basoulis, D.; Pavlopoulou, I.; Darema, M.; Deliolanis, J.; Daikos, G.L.; Boletis, J.; Psichogiou, M. Bloodstream infections by gram-negative bacteria in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outcome. Transpl. Infect. Dis. 2020, 22, e13442.
[20] 19.Aslam S, Rotstein C: Candida infection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Guidelines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Clin Transplant 2019; 33(9):e13623.
[21] Husain S, Camargo JF: Invasive Aspergillosis in solid-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Guidelines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Clin Transplant 2019; 33(9):e13544.
[22] Baddley JW, Forrest GN: Cryptococcosi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Guidelines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Clin Transplant 2019; 33(9):e13543.
[23] Fishman JA, Gans H: Pneumocystis jiroveci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Guidelines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Clin Transplant 2019; 33(9):e13587.
[24] RAZONABLE R R, HUMAR A. Cytomegaloviru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Guideline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J/OL]. Clinical Transplantation, 2019, 33(9)[2022-11-0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tr.13512. DOI:10.1111/ctr.13512.
[25] Dulek, D.E.; Mueller, N.J. Pneumonia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Guidelines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Clin. Transplant. 2019, 33, e13545.
[26] MOSSAD SB. Management of infection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J]. Infect Dis Clin North Am, 2018, 32(3):xiii-xvii. D
[27] Anesi JA, Blumberg EA, Abbo LM. Perioperative antibiotic prophylaxis to prevent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 2018;102(1):21-34.
[28] BIAS TE, MALAT GE, LEE DH, et al. Clinical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in abdominal solid organ transplant (SOT) recipients[J]. Infect Dis (Lond), 2018, 50(1):67- 70.
[29] Bodro, M.; Linares, L.; Chiang, D.; Moreno, A.; Cervera, C. Managing 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in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Expert Rev. Anti. Infect. Ther. 2018, 16, 723–732
[30] Wojarski J,Ochman M,Medrala W,et al. Bacterial infections during hospital stay and their impact on mortality after lung transplantation: a single-center study[J]. Transplant Proc,2018,50( 7) : 2064 - 2069.
[31] Christopher H , Christopher C , Beth C , et al. Heart transplantation[J]. Annals of
[32] Cardiothoracic Surgery, 2018, 7(1):172-172.
[33] Rossano JW,Cherikh WS,Chambers DC,et al. The regist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 twentieth pediatric heart transplantation report—2017; focus theme: allograft ischemic time[J]. J Heart Lung Transplant,2017,36( 10) : 1060 - 1069.
[34] ZHANG R, LIU L, ZHOU H, et al. Nationwide surveillance of clinical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strains in China[J]. EBioMedicine, 2017, 19:98-106.
[35] Anesi JA, Baddley JW: Approach to the Solid Organ Transplant Patient with Suspected Fungal Infection. Infect Dis Clin North Am 2016; 30(1):277-296.
[36] Nett JE, Andes DR: Antifungal Agents: Spectrum of Activity, Pharmacology, and Clinical Indications. Infect Dis Clin North Am 2016; 30(1):51-83.
[37] Gavaldà J, Meije Y, Fortún J, et al: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4; 20 Suppl 7:27-48.
[38] HIRSCH H H, RANDHAWA P, THE AST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BK Polyomaviru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BK Polyomaviru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J/OL].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2013, 13(s4): 179-188. DOI:10.1111/ajt.12110.
[39] ISON M G, GROSSI P, THE AST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TY OF PRACTICE. Donor-Derived Infection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Donor-Derived Infection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J/OL].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2013, 13(s4): 22-30. DOI:10.1111/ajt.12095.
[40] Cornely OA, Bassetti M, Calandra T, et al: ESCMID*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Candida diseases 2012: non-neutropenic adult patients.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2; 18 Suppl 7:19-37.
[41] Grossi PA, Gasperina DD, Barchiesi F, et al: Italian guidelines for diagn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in 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Transplant Proc 2011; 43(6):2463-2471.
[42] EID A J, RAZONABLE R R.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after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J/OL]. Drugs, 2010, 70(8): 965-981. DOI:10.2165/10898540-000000000-00000.
[43] Dromer F, Bernede-Bauduin C, Guillemot D, et al: Major role for amphotericin B-flucytosine combination in severe cryptococcosis. PloS one 2008; 3(8):e2870.
[44] Borro JM, Solé A, de la Torre M, et al: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inhaled amphotericin B lipid complex (Abelcet) in the prophylaxis of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s following lung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 Proc 2008; 40(9):3090-3093.
[45] Saad AH, DePestel DD, Carver P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gnitud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drug interactions between azole antifungals and select immunosuppressants. Pharmacotherapy 2006; 26(12):1730-1744.

蔡常洁 教授
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学会生命支持(ELSO)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感染学组委员
中华肝病学会感染学组委员
中国灾难预防医学分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菌防治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肠内与肠外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肝病学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肠内与肠外营养杂志》、《器官移植杂志》编委
从事重症医学临床工作30年,尤其是对严重感染、肝功能损害、重症胰腺炎、营养支持、凝血功能紊乱的纠正、器官功能衰竭与维护有深厚造诣,是国内著名的肝移植、肝脏外科重症监护治疗专家,曾先后指导国内50余家医院的肝脏移植术后监护治疗工作。
- 评价此内容
- 我要打分
近期推荐
热门关键词
最新会议
- 2013循证医学和实效研究方法学研讨会
- 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
- 世界帕金森病和相关疾病2013年会议
- 英国介入放射学学会2013年第25届年会
- 美国血液学会2013年年会
- 美国癫痫学会2013年第67届年会
- 肥胖学会 2013年年会
- 2013年第9届欧洲抗体会议
- 国际精神病学协会 2013年会议
- 妇科肿瘤2013年第18届大会
- 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学会2013年第29届…
- 2013年第4届亚太地区骨质疏松症会议
- 皮肤病协会国际2013年会议
- 世界糖尿病2013年大会
- 2013年国际成瘾性药年会
- 彭晓霞---诊断试验的Meta分析
- 武姗姗---累积Meta分析和TSA分析
- 孙凤---Network Meta分析
- 杨智荣---Cochrane综述实战经验分享
- 杨祖耀---疾病频率资料的Meta分析
合作伙伴
Copyright g-medo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环球医学资讯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网络实名:环球医学:京ICP备08004413号-2
关于我们|
我们的服务|版权及责任声明|联系我们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京)-经营性-2017-0027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复核同意书 京卫计网审[2015]第034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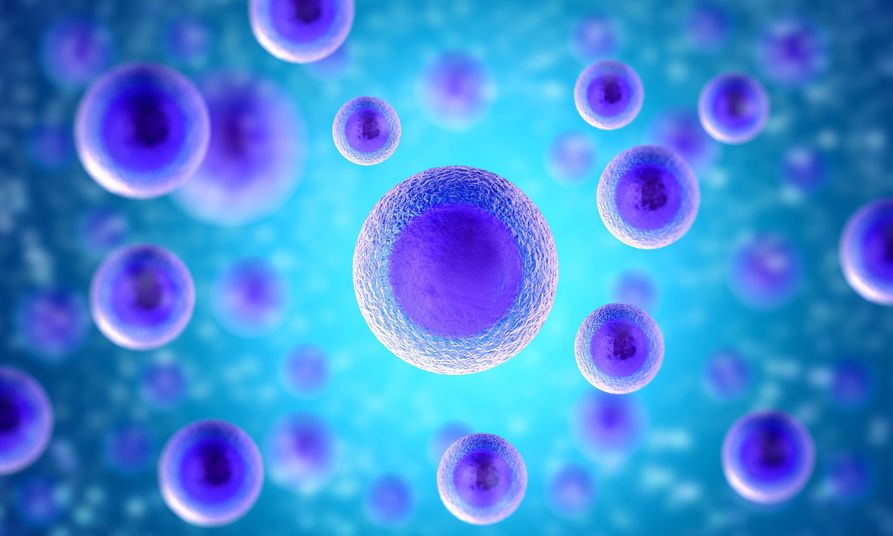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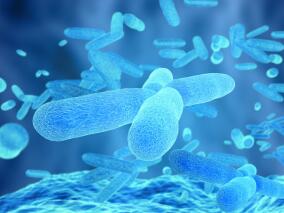

 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

